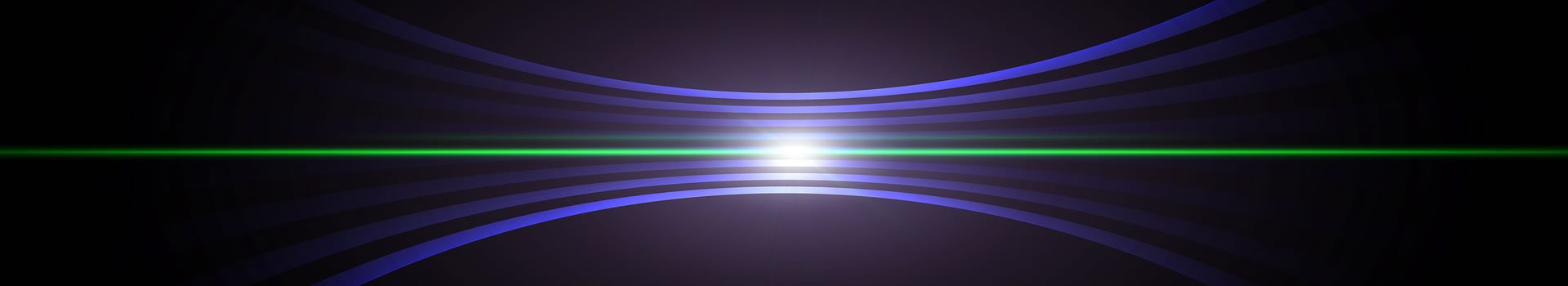

1951年,陈晓农随父亲陈伯达踏入中南海,直至1966年的岁末,陈氏家族才迁出那道深红宫墙,在这座宏伟的庭院中度过了整整十五年的岁月。
初踏足中南海的陈家,便安置于勤政殿内的两间宽敞之室。勤政殿与毛泽东所居的丰泽园毗邻,该殿乃一栋融合了西式风格的建筑。追溯至民国初期,袁世凯曾在此办公。
坐落在勤政殿与丰泽园之南的方位,不远便可见到那赫赫有名的瀛台。瀛台四周环绕着碧波荡漾的湖水,其北侧架设着一座桥梁,通向湖岸。岛上分布着几座殿堂,屋顶尖端铺着金黄色的琉璃瓦,门柱涂以鲜艳的红漆,因清末时期曾关押光绪皇帝而成为了众多文艺作品描绘的焦点。陈晓农幼年时,曾多次跟随长辈游览瀛台,如今在他记忆中,那里显得异常宁静,静得仿佛连乌鸦的叫声都未曾响起。
陈伯达并未在勤政殿久留,便搬迁至中海岸边一处由四合院组合而成的连体住所,居于最北端的院落,该处通常被称作“迎春堂”。传闻,这栋建筑在清代曾是宫廷太监们的居所。陈伯达入住时,院落尚存旧日的颓败之态,门柱上的漆面已斑驳脱落,屋顶之上长满了青苔,然而屋内却已配备了暖气与卫生间。
随着中南海的分区管理,南北方向被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区域,并在各分界线的路口设置了岗哨。陈伯达一家的住所恰好位于中南海的乙区。乙区居民可自由出入丙区,但若想前往甲区,则需严格遵守规定。这让年轻的陈晓农深感惋惜,因为从此他再也无法随意前往南海的瀛台等地游玩。
甲区居住着中央的众多主要领导人,其中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同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及毛泽东的私人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以及卫士长李银桥,亦同住于此。而时任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长的汪东兴,则居于中南海东岸的西苑门内,一个隶属于乙区的独立区域——“东八所”。
乙区的长居居民包括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等知名人士,而之后,邓小平、陈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亦相继迁居于此。
丙区居民以国务院系统的高级领导为主,其中包括周恩来、李先念、林伯渠等众多杰出人物。
中南海深处,一条柏油铺就的马路沿湖西畔蜿蜒,南北贯通。在这条路南端,通往毛主席居住地的路口处,设有甲乙两区间的关键岗哨。日间,岗亭栏杆常闭,严格限制车辆通行。而当夜幕降临,岗哨敞开大门,允许车辆通行。这是因为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人惯于夜间办公,白日则安寝休息。
每至周末,甲区内设有两处热门去处,乙区的居民得以自由出入。其中一地为名为“春藕斋”的餐馆,另一则是颇受欢迎的“西楼餐厅”。
春藕斋坐落在颐年堂畔,是周末欢聚舞会的热门场所,亦偶尔上演光影盛宴。陈晓农回忆起自己曾造访此地五次六回,其中一次是观赏成年人的翩翩舞姿,其余几次则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
西楼餐厅坐落于中南海西大门的南侧,昔日曾是一家特设的灶台食堂。餐厅空间宽敞,光线充足,地面铺设着天然的木地板,而东西两侧的入口则由警卫严密守护。
西楼餐厅偶尔也会举办电影放映活动,需购票入场。票价方面,普通电影每张仅需两角,而上下集连映的电影则需三角,与当时市面上的电影院票价相仿。放映的影片以国产电影为主,亦涵盖苏联及友好国家的作品,偶尔亦会播放来自香港的影片。
中南海内,警卫战士的身影尤为常见,然而他们却无法融入居民的娱乐生活,因此西楼餐厅的电影放映,观众数量并不众多。定期观影的人群,包括大人与孩童,总计不过百余人。在领导人中,李富春与蔡畅夫妇、杨尚昆与李伯钊夫妇是常客。刘少奇、朱德、陆定一、胡乔木等偶尔也会光顾,他们观看的多为国产新片,这些影片属于“审查片”范畴。而其他领导人则鲜少踏足电影院。
在经济困境的严峻时期,中南海的居民与北京市的广大民众共同承受了食品短缺的艰辛。在粮食供应依赖粮票的时代,无论是红墙之内还是之外,人们的饮食状况并无二致。
在位于中南海东门外北长街的一处院落中,设有一个被称作“供应站”的机构。这里,中南海内的特灶食堂与小灶食堂,以及那些独立设灶为领导人烹饪的厨师,均会在此购置所需食材。此外,那些市面上难以寻觅的知名烟草与美酒,亦可在该处购得,然而其购买量受到严格限制,需依照特供证所规定的定量进行供应。
陈晓农与刘叔宴。(继母)谈及此事,一位同学便提及,其父在参与中央会议或是外出公干时,用餐无需兑换粮票,因此他们家的粮票颇为充裕。然而,陈晓农却表示自家粮票颇为紧张,这让同学们都感到难以置信。
刘叔眉头紧锁,感慨道:“怎么会有这种情形?绝不可能!你父亲参加任何会议,都是需要粮票的。”
陈晓农反问:“难道不能选择不交吗?你们偏要这么做?”
刘叔回忆道:“不久前,你父亲前往庐山参加中央会议,连会议通知上都明确要求携带粮票。我们每次参会,无不严格遵守规定,从未有过例外。而我们家的粮票,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陈晓农问:“爸爸粮食定量多少?”
刘叔在宴会上解释道:“机关规定我们先行提出具体的数量,你父亲申报的是21斤,因此便按照21斤来定。而我上报的数字比父亲多了3斤,所以最终定为24斤。”
还有一事,陈晓农至今仍铭记于心。那是在他于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生涯中,某个周末归家,与家人围坐餐桌共进晚餐之际,他提及了一位同学的往事:“我曾从同学那里听闻,他初中就读于八一学校——”军队干部子弟校求学岁月。他曾言,那段最艰辛的时光,即便在八一学校,粮食也常告急。学校便设法购得了一批无需粮票的高级点心,用以分食于同窗们。然有一部分同学却不愿享用,竟将点心随手丢弃。
“切莫再言语!”陈伯达骤然怒吼一声。
“且慢如此,不妨倾听一下孩子们的述说,从中或许能洞察一二。”刘叔平静地开口说道。
陈伯达将空碗重重地置于桌面,随即起身,步入书房。
“爸怎么了?”陈晓农不解。
刘叔宴叹道:“唉,近两年来,国家经济面临困境,粮食供应紧张,竟还有人如此挥霍粮食!你父亲对此深感愤慨。如今,他甚至不愿食用按规定供应的鸡蛋,因为他深知国家正将鸡蛋出口,用以换取急需的农业机械。不久前,办公厅负责伙食的人员还曾劝说过你父亲。”
在五六十年代,中南海中高层领导的饮食状况各有差异。负责安排领导饮食的机构为西楼餐厅,亦被称为特灶食堂。日日直接光顾西楼餐厅进餐的领导,包括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人;而仅有陈伯达一家选择在此取餐后带回家自行烹饪。
陈晓农随李景如。(陈伯达的公务员)在西楼餐厅取餐途中,我坐在大厅中央的桌边等待,这时一位管理员走过来与他们闲谈。他评论道:“你们家的菜肴制作简便,很快就能上桌。家里应该有五六个成员吧?每月的伙食费大约在八九十元,最多不超过一百零几元,这在附近算是很便宜的。林伯渠老先生和老夫人每月的花销就要超过八十元。不过,他们两位收入较高,年纪也大了,身边又没有子女照顾,吃得好些也是理所当然的……”
关于他人的饮食状况,陈晓农并无确切听闻。然而,他深知刘少奇一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十分宽裕。刘少奇除了三个成年子女已各自成家立业,其余五个子女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均与刘少奇及王光美一同在西楼餐厅用餐。陈晓农提及,他最为熟悉的便是丁丁。(刘允真)此情形下,可见一斑。
丁丁与陈晓农同年出生,1953年,他们在北京育英小学成为了同窗之谊。育英小学,作为一所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学校,其校舍与设施在北京市内堪称一流,学生的食宿及衣物皆由学校全面负责。然而,学校的地理位置略显偏僻,坐落于北京西郊的万寿路附近。尽管孩子们都是寄宿制,但此地却缺乏公共交通,每周六日,孩子们需依靠各机关派出的班车来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
1957年夏日,中央作出决定,撤销了干部子弟学校的体制,自此,学生费用全数由已实行薪金制的家长承担。这其中包括了学杂费,以及每月三十余元的食宿费。然而,刘少奇家中子女众多,若皆选择住校,经济负担将不堪重负。为了削减开支,刘家决定让丁丁转学至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师大附小,改为走读,这样一来,至少可以省去住宿费用。
刘少奇一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而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李富春与蔡畅夫妇亦面临着粮票短缺的困境。彼时,他们年迈的父母与外孙安德列同住。安德列的小名带有俄国风味,这源于他的父亲是苏联人。
曾经,不知何故,安德列习惯于独自前往西楼餐厅享用餐点。那日,陈晓农与李玉元(陈伯达的公务员)前往食堂途中,偶遇一名厨师正在斥责安德列。二人见此情景,便挪步至东墙边摆放的椅子上坐下。不久,安德列离开了。李玉元随后询问厨师:“发生了何事?”厨师回应道:“安德列已经连续几天未出示粮票用餐,这怎么可以?我正在对他进行政治教育,敦促他尽快补缴粮票。”
中南海里居住的少年儿童本来就很少,可大人还常常告诫孩子们:“切勿随意串门!”这是因为国家领导人多在家中处理公务,孩子们的探访或许会打扰到他们的工作。尽管中南海并非每三步就设一岗,每五步就设一哨,但岗哨的数量亦颇为可观。不仅在甲乙丙三区分界路口设有岗哨,就连重要领导人的住宅门前也增设了岗哨。这一切都让小朋友们心生畏惧,自然而然地缩小了他们的活动区域。
在中南海的院落深处,领导人私下走访的情况并不常见。然而,那些曾踏入陈伯达府邸的领导,陈晓农都能清晰回忆。他记得朱德曾来访一次,那是在陈伯达迁至迎春堂之初。彭德怀夫妇共来访过三次。陈毅在中南海安家之初,曾单独造访一次,后来又与周恩来总理一同来访。周恩来总理在1965年独自来访过一次。胡乔木和陆定一各来访过两次。彭真来访的次数相对较多,陈伯达也曾拜访过位于台基厂的彭宅,并带陈晓农一同前往。康生来访过三次,而陈伯达也回访过康家。陶铸在来京开会期间,来访过两三次。李雪峰夫妇来访过一次。周扬来访过两三次。王震来访过一次。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叶飞……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带领福建干部共十几人来访陈伯达,福建惠安人。此外,陈伯达曾携陈晓农一同拜访过张鼎丞的住所。
田家英在五十年代初期与陈伯达来往频繁,后来就逐渐减少了。陈晓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53年3月5日,那天晚上天黑不久,田家英来了,一脸的愁容,坐下后耷拉着脑袋对陈伯达说:“斯大林同志已经离世,电台刚刚播报了这一消息。”言毕,他泪水横飞,呜咽不止。陈伯达则紧锁双眉,面容凝重,沉默不语。
稍后,陈伯达询问:“主席是否已得知此事?”
田家英轻轻摇头,说道:“尚且不知情,尚未告知于他。”
陈伯达提议道:“那么,我们就一同前往他处吧。”言罢,他起身,与田并肩走出家门。
陈晓农曾在怀仁堂观看陈伯达看戏之际,远远地目睹了毛主席两次身影。而真正与之面对面相遇,则是在1960年4月30日于天津的那一天。
那一年,陈伯达莅临天津开展工业调研工作。正值“五一”假期,他特意将家人从故乡接到天津,共度佳节。4月30日的午后,刘叔在家中设宴款待。(继母)携陈晓农及其两位妹妹抵达天津,当晚,我们全家齐聚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共度欢乐时光。
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其宏伟壮观,昔为外国人士及富豪雅集之所,解放之后,转型为服务于干部们的娱乐俱乐部。陈晓农提及,即便是在繁华的京城,他也未曾目睹如此设施齐全、豪华典雅的综合性娱乐圣地。
他们首先参观了俱乐部的室内游泳池。该游泳池明亮宽敞,其面积甚至超过了中南海内的室内游泳池,装饰亦更为精致。彼时,偌大的泳池中仅见杨尚昆一人悠然自得地游泳,其神情显得格外惬意。正当他们观察之际,有人告知,毛主席此刻亦身处干部俱乐部,杨尚昆正是陪同毛主席一同前来的。
随后,他们抵达地球。(保龄球)在这间宽敞的室内,孩子们短暂地沉浸在地球的奇幻世界中。刘叔的心情愉悦,他笑容满面地对三个孩子说:“今天,我要让你们这些小乡巴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他们在地球体验馆中流连忘返,畅快淋漓地体验过后,便来到了一个别致的小型演出厅。此时,毛主席正坐在厅中央的一张长沙发上,饶有兴致地观赏着折子戏。一个年仅十岁的小演员扮演着孙悟空,身姿矫健,腾挪跳跃,令人目不暇接。毛主席看得喜不自胜。戏幕落下,他笑容满面地询问起小演员的年龄和身世。
此刻,陈伯达转身向三个孩子提议:“我来带你们去见一见毛主席,如何?”孩子们激动地频频点头。趁着小演员尚未退场,陈伯达迈步走到毛泽东的背后,轻声说道:“主席,这些孩子们都十分希望能见到您。”话音未落,毛主席便立刻起身。陈晓农与他的两个妹妹立刻上前,逐一向毛主席伸出了手。握手之际,他们均用双手紧握毛主席的双手,然而彼此并未开口交谈,现场气氛显得格外庄重。事后,刘叔宴对孩子们说:“你们在见毛主席的时候,确实有些紧张了,连问候一句‘毛主席好’都没有。”
数载之后,陈晓农得悉毛泽东的贴身卫士李银桥回忆起毛泽东接见访客的情景:他素有卧床处理公务的习惯。李银桥曾亲眼目睹,每当国家、政府及军队的领导人前来请示或汇报工作,毛泽东往往依旧安坐,埋头批阅文件。有时,他只是聆听几句汇报,便以手势示意:“坐吧,请坐下来谈。”若毛泽东身处沙发上,即便党内同志来访,他亦很少起身,仅以手势邀请对方落座,坐下后便直截了当地讨论事宜,言辞间鲜有闲谈。
显而易见,当毛主席亲切接见陈晓农兄妹之际,他起身离座,这一行为实属破格。尽管毛主席身处公众视野之中,然而那不过是一场轻松愉快的聚会,无需过分拘泥于礼节。再者,那三位孩子不过是他下属的儿女罢了。
继而,陈晓农心生遐想:毛主席之所以如此郑重地自沙发起身,亲自接见他们三兄妹,或许是因为毛主席早已洞悉了其兄长陈小达不幸丧生的真相。而当时,这一信息尚未透露给陈伯达本人。
自1955年起,中央警卫局正式确立了中南海门卫的礼仪规范,要求对出入大门的领导人必须执行军礼。因此,每当陈伯达乘坐的灰色吉姆牌轿车驶入或离开中南海,大门口的值班军官便会一眼认出,随即高声呼喊:“敬礼!”紧接着,门柱两侧的卫士迅速挺身,肃立行礼。
然而,陈伯达在闲暇时分,常独自徒步穿过西门,乘坐14路公交车前往琉璃厂的老书店搜寻书籍。据陈晓农所述,他本人曾两次陪同陈伯达一同步行出西门。当两人站在门口内侧,那位早已熟识陈伯达的值勤军官,在陈伯达走近时,突然高声呼喊:“敬礼!”随即,卫兵们纷纷举手行礼。陈伯达也急忙边走边举起右手以示回礼。这一过分庄重的仪式,让年轻的陈晓农感到极不自在,几乎想要立刻跨出大门。幸运的是,当时府右街上的行人稀少,并未引来众人围观。
传闻中,警卫部门曾向上级汇报了这一状况,并指出若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察觉到其中的规律,凭借是否行礼来辨识出入者的身份,进而追踪步行离去的领导人,将大大增加安全风险。鉴于此,取消对步行者行礼的做法便成了必然之举。
陈伯达于步履中南海西门时,受到了应有的尊敬,然而,在他踏入北门之时,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对待。
在一个阳光斜照的午后,陈晓农与陈伯达漫步北门而出,径直前往北海大桥东侧的团城参观工艺美术展览。数小时后,两人依旧步行返回。夜幕初降,守门的卫兵已更换了班次。陈伯达往常鲜少步行进出此门,因此卫兵对他并不熟悉,按照规定,对他出入证件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出入证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亲自签发,自无任何疑虑。然而,证上所列“陈伯达”之名,却让守卫显得陌生异常,加之证上的职务一栏竟是空白。在当时,中南海内的高级干部鲜少步出宫门,卫兵们未曾亲历过查验高级干部的出入证,更别提遇见过职务栏空白的出入证了。
守卫疑惑地询问:“为何这一栏未填写职务信息?”
陈伯达不紧不慢地回应道:“发来的就是这样,我亦不知其所以然。”
卫兵道:“你去警卫室。”
陈伯达带着陈晓农一起步入门内东侧的警卫室。一个军官态度还算和气,让他们先坐下,自己起身到里间屋去打电话请示领导。不一会儿, 军官走出来,连声说对不起。陈伯达说:“没关系,你们做得很对。”
原本这不过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意外地在中南海传为佳话。到了1990年,陈晓农的妻子张兰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当时,该所办公室的副主任邹本浩曾在胡乔木身边任职。在一次闲谈中,他们提及此事,仍不禁相视而笑。原来,当年人们听闻陈伯达不拘小节,身着布衣旧衫,竟被守卫误认为是流浪老人,被拦在门外仔细盘查了许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