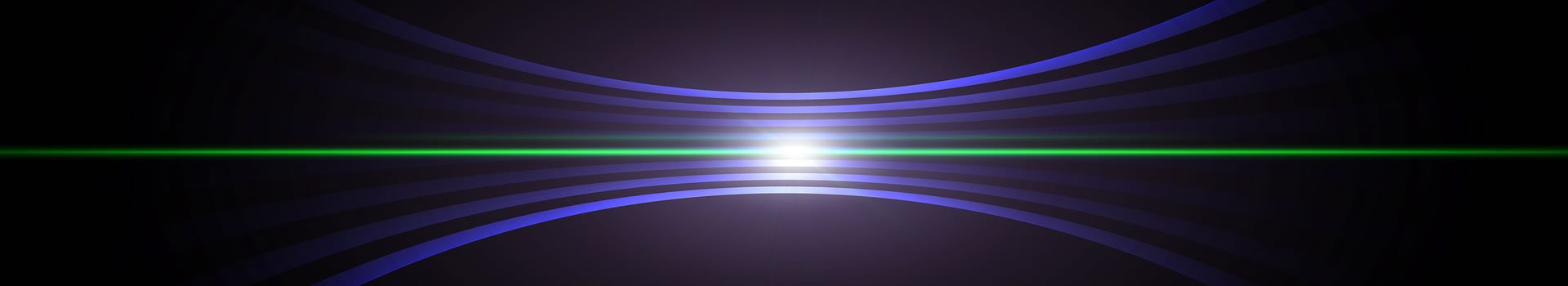
第一章:天主配对的政治婚姻
1554年盛夏,英格兰汉普郡的温彻斯特大教堂,阴霾的天空未能阻挡一场震动欧洲的婚礼。
西班牙王储,未来的国王腓力二世,身着华贵的黑色天鹅绒礼服,胸前缀满哈布斯堡家族金羊毛骑士团的徽章,步入了这座古老的圣殿。

他时年二十七岁,面容清癯,眼神冷静,步伐中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矜持与疏离。
他的新娘,是比他年长十一岁的英格兰女王玛丽·都铎。玛丽站在祭坛前,一身深红镶金线的礼袍,像一团燃烧的、略带疲惫的火焰。
她的眼中闪烁着近乎狂喜的光芒,这光芒不仅源于对婚姻的憧憬,更源于对信仰的执着。
在她看来,这场婚姻是天主的旨意,是将被新教异端玷污的英格兰重新拉回天主教正统怀抱的神圣联盟。
而腓力,这位来自欧洲最强大天主教帝国的继承人,就是天主赐予她的工具与伴侣。
然而,在这看似神圣的联姻背后,隐藏着一段更为现实与冷酷的政治安排。
曾几何时,玛丽心中期盼的联姻对象,并非眼前这位年轻寡言的王子,而是他的父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她血缘上的表兄。查理五世,这位欧洲的霸主,在玛丽最为困顿的岁月里,曾是她精神上的遥远依靠和潜在的保护者。
她曾幻想过,成熟、强大且同样虔诚的表兄,能成为她拯救英格兰的完美伴侣与指引。
但政治棋局从不依赖于个人的浪漫遐想。早已娶妻的查理五世,以帝国利益为最高准则,冷静地审视着棋盘。在他眼中,正值盛年、且将成为西班牙国王的儿子腓力,是维系与英格兰联盟更合适、也更可控的棋子。
于是,他向玛丽提出了这个“更佳”的建议,将原本可能属于父亲的婚约,如同交接一件重要的政治遗产般,传递给了儿子。
玛丽接受了,带着一丝对未竟幻想的失落,但更多的,是将此视为查理五世(和她共同的天主信仰)对她事业支持的象征,并将所有对庇护与情感的渴望,转移到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丈夫身上。
腓力微微躬身,执起玛丽的手,触感微凉而略显粗糙。他遵循礼仪,在她面颊上印下合乎规范的一吻。他的心中没有多少新郎应有的悸动,更多的是对使命的清醒认知。
他的父亲,查理五世,在他临行前谆谆告诫:“我的儿子,这并非一桩普通的婚姻。这是哈布斯堡王朝伸向不列颠的触角,是遏制法兰西野心的关键,是守护基督信仰世界的基石。让那个女人快乐,但记住,西班牙的利益高于一切。”
他深知,自己既是新郎,也是父亲(乃至帝国)意志的执行者,步入这场由长辈精心策划的联盟。
洞房花烛夜,宫殿的寝室奢华却难掩英伦的湿冷。玛丽望向她的丈夫,眼中是毫不掩饰的爱慕与恳求。她渴望的,不仅是一个政治盟友,更是一个能温暖她孤寂半生的男人。
她絮絮叨叨地诉说着她童年的苦难,母亲凯瑟琳被废的屈辱,她自己在弟弟爱德华六世新教政权下如履薄冰的岁月,以及她如何凭借坚定的信仰重登王位。
或许,在某个瞬间,她看着腓力那与他父亲有几分相似的、冷峻的哈布斯堡面容,心中掠过的,是那个她从未得到过的、来自皇帝表兄的庇护幻影。
腓力耐心听着,偶尔点头,用他熟练的拉丁语和缓慢的西班牙腔法语回应。
他确实对这位命运多舛的女王产生了一丝怜悯。她的虔诚、她的坚韧,以及她对他几乎卑微的依赖,都触动了他内心深处那为数不多的柔软之地。
他并非铁石心肠,在这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玛丽的热忱是他唯一能感受到的、带着温度的东西。
他会与她同寝,履行丈夫的职责,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现出适当的亲密,以稳固她的情绪和她的王权。
然而,他的情意是有限的,如同账本上谨慎拨出的款项,永远无法与他对权势的考量相提并论。
当玛丽依偎在他怀中,憧憬着共同治理英格兰,孕育继承人时,腓力脑中盘算的,是如何利用“英格兰国王”(他与玛丽共治的头衔)的身份,调动英国舰队与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协同作战,对抗老对手法兰西。
他敦促玛丽重启异端审判,烈火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熊熊燃烧,近三百名新教徒被处以火刑,为玛丽赢得了“血腥玛丽”的恶名。
腓力私下里认为手段过于酷烈,可能引发民变,但他并未强力阻止——只要这能净化英格兰的信仰,巩固天主教阵营,便符合西班牙的核心利益。
那一点点因怜悯而生的情意,在宏大的政治蓝图面前,轻如鸿毛。而这幅蓝图的初稿,甚至并非由他亲手绘制,而是源自他父亲那更为老谋深算的布局。
他只是在忠实执行,并试图在此基础上,绘就更辉煌的帝国篇章。
第二章:镜花水月与权力真空
命运的残酷超乎想象。玛丽两次宣布怀孕,腹地隆起,满朝欢庆,腓力也一度燃起希望——一个流淌着哈布斯堡和都铎血液的继承人,将把英格兰永久纳入西班牙的势力范围。
他甚至在玛丽第一次“怀孕”期间,获得了在玛丽缺席时代行国王权力的委任状。
然而,两次“妊娠”最终都被证明是假孕,可能是玛丽极度渴望子嗣导致的生理紊乱。
希望如肥皂泡般破灭,腓力的耐心也随之消磨殆尽。他对玛丽的身体失去了兴趣,那曾经引发他一丝怜悯的躯体现在只代表着失败与徒劳。
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腓力继位为西班牙国王,事务愈发繁忙。他留在英格兰的时间越来越少,最后几乎常驻欧陆。
玛丽的心在一次次失望和丈夫的疏远中渐渐枯萎。她写给腓力的信件充满了哀怨与思念,而腓力的回信则日益简短、公式化,内容多关乎战争借款、军队调度和宗教政策。
1558年,英军在欧洲大陆丢失了最后的欧陆据点加来,玛丽陷入彻底的绝望,认为这是天主的惩罚。
同年,她病入膏肓。
腓力得知消息时,正在处理尼德兰棘手的叛乱。他派来了使者表达慰问,但本人并未现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玛丽泪流满面,对侍从低语,说她死后,若进行尸检,人们会发现“Calais”刻在她的心上。
至死,她都深爱着她的丈夫,并为未能为他生下继承人和保住国土而痛彻心扉。
腓力对玛丽的死,或许有一瞬间的黯然,毕竟那是一个曾全心爱慕他的女人。但更多的,是一种紧迫感。
玛丽无嗣而终,根据遗嘱和英国法律,王位将由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安妮·博林的女儿伊丽莎白继承。
伊丽莎白!这个名字让腓力眉头紧锁。
她年轻,聪明,受过极好的教育,而且——最关键的是——她是一个新教徒,或者说,至少被普遍认为是新教徒。
让这样一个女人成为英格兰女王,对西班牙的天主教事业和地缘政治将是巨大的威胁。
第三章:新的棋局与危险的诱惑
伊丽莎白一世加冕了。她的登场如同一道清冽的光芒,划破了“血腥玛丽”统治下的阴郁。
她谨慎地推行宗教和解,试图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找到一条让英格兰能够安定下来的中间道路。她的魅力、智慧和活力,迅速赢得了臣民的爱戴。
腓力迅速调整了策略。他向伊丽莎白提出了联姻的请求。这在外人看来或许不可思议——刚刚丧偶,就向亡妻的妹妹,且是信仰异端的妹妹求婚?
但在腓力以及许多欧洲宫廷的政治家眼中,这再合理不过。
首先,这能维持西班牙对英格兰的影响力,防止其彻底倒向法兰西(法国王子也在追求伊丽莎白)。
其次,腓力自信地认为,只要伊丽莎白嫁给他,他就能引导甚至迫使她回归天主教。在他心中,这不仅是政治联姻,更是一场针对异端女王的“信仰征伐”。
然而,伊丽莎白早已不是那个在姐姐统治下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公主了。她深刻理解权力的本质,尤其是婚姻可能带来的桎梏。
她巧妙地运用她的未婚状态作为外交筹码,在西班牙、法兰西等求婚者之间周旋,为初生的英格兰政权争取喘息的空间。
对于腓力的求婚,她既不明确拒绝,也不欣然接受。她与腓力的使者谈笑风生,称赞腓力陛下的威严与智慧,但对婚姻事宜始终含糊其辞。
她甚至允许一种微妙的氛围产生——仿佛她对这位曾经的姐夫,保有某种特殊的好感。
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反而激起了腓力一种复杂的情感。
这与玛丽当年毫无保留的热情截然不同。伊丽莎白像一头难以驯服的猎豹,优雅、敏捷,充满了危险的吸引力。
他或许在某个瞬间,超越纯粹的政治计算,对这个与他智力相当、甚至更胜一筹的女人,产生了一丝欣赏乃至征服的欲望。
他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大使,指示他不仅要强调联姻的政治和宗教益处,也要适时地表达国王个人对女王陛下的“崇高敬意与日益增长的兴趣”。
但这缕情意,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只在腓力精密计算的心湖中激起一圈微澜,旋即消失。
当伊丽莎白的表现越来越显示出她无意在宗教上做出根本性让步,当英格兰的海盗(如德雷克)开始肆无忌惮地劫掠西班牙从新大陆运载金银的船只,腓力的耐心再次耗尽。
他意识到,伊丽莎白不会成为他棋盘上任他摆布的棋子,她本身就是一位高超的棋手。
第四章:无敌舰队的怒火与情意的灰烬
年复一年,腓力与伊丽莎白的关系从潜在的婚姻联盟,滑向了公开的敌对。
伊丽莎白支持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她的海盗们继续挑战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而她最终处决了拥有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的苏格兰天主教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这一举动,在虔诚信奉天主教的腓力看来,是对君主神圣权利的亵渎,是踩过了最后的红线。
所有曾经可能存在过的、对伊丽莎白那一点点基于欣赏的模糊情意,此刻全部转化为被羞辱、被挑衅的怒火。
他心中那个曾经可能成为西班牙王后的聪明女人,现在在他眼中,成了一个“异端婊子”、“那个英格兰女人的私生女”(他拒绝承认伊丽莎白的合法身份)、魔鬼在人间的代理人。
他决心动用帝国的全部力量,彻底征服英格兰。在埃斯科里亚尔修道宫的寂静书房里,腓力夜以继日地工作,亲自审阅无敌舰队每一艘战舰的设计图,过问每一门火炮的铸造,审批庞大的军费开支。
他的梦想,不再是娶一位英格兰女王,而是为天主夺回一个迷失的王国,并一劳永逸地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
1588年,庞大的“最幸运的无敌舰队”终于起航。然而,命运再次嘲弄了腓力。
风暴、火攻、以及英国海军灵活的战术,使得这支寄托了他全部野望的舰队损失惨重,折戟沉沙。
消息传来时,腓力正在埃斯科里亚尔的教堂祈祷。他沉默地听完了噩耗,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我派遣舰队去与英格兰人作战,而非与狂风巨浪。” 他接受了这次失败,如同接受命运的无常,并将之归因于天主的意旨,转而更加虔诚地投入到祈祷和治理他庞大的帝国中。
然而,在无数个深夜里,当他独自面对烛光,地图上英格兰的轮廓是否还会勾起他一丝复杂的回忆?
那个依赖他、爱慕他最终心碎而亡的玛丽,她的面孔是否曾与那个机智、冷漠、最终彻底击败他的伊丽莎白的面孔重叠?
或许有过一瞬。但对他而言,无论是玛丽那带着温度却最终无用的爱,还是伊丽莎白那充满挑战却终究危险的魅力,都早已在西班牙帝国黄金般的宏图霸业中,冷却、风干,化为历史的尘埃,与权力博弈中几不可察的一缕微尘。
他首先是西班牙的国王,天主在尘世的战士,然后,才短暂地、有限地,成为过两个女人的丈夫和求婚者。
情意只是权力的点缀,而权力,才是他永恒的信仰。

